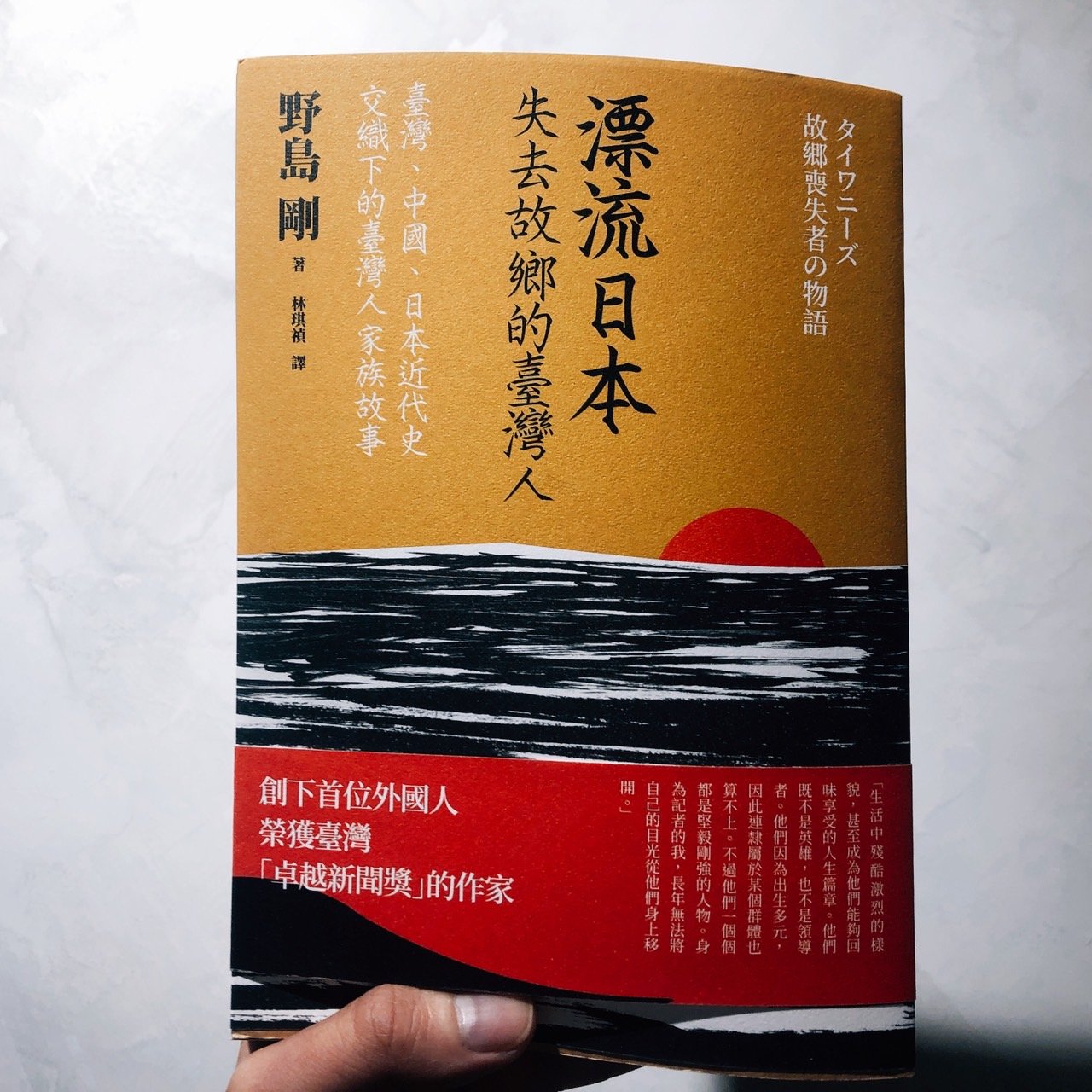粉紅色的底座,上半部是常見細窄的白色欄杆,長47公分、寬57公分、高46公分,這原本是用來飼養小動物的柵籠。然而,裡頭不只關過兔子,還曾囚禁過一名發育遲緩、體重過輕,有語言表達障礙,至今仍找不到屍骨的三歲小男孩——皆川玲空斗。
自事件被報導以來,皆川家周遭的鄰居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便表示過:「皆川一家人常常到了晚上就開車外出,直到深夜大約一、兩點左右才回到家,晝伏夜出的生活習慣與一般人都不同;隱約知道他們家中有不少小孩,較常遇到的僅有其中四個,但像是次子玲空斗和次女玲花就沒有那麼常見到。」
而關於次子玲空斗的死,根據他父母親的陳述:「前一天還很有精神,但隔天早上醒來,發現他已經完全沒了呼吸。」乍聽之下,看似無異卻又有些不太自然。2014 年,當社福機構與警察介入調查才發現,實際上玲空斗小弟弟早在一年三個月前就死亡了──這不禁令院方和警方懷疑,他的屍體被丟棄在哪兒?他的死因又究竟為何?
疑似孩童受虐失蹤的通報

這起發生在宛若完美密室般的自家當中、兇手還是親生父母的孩童虐殺致死事件,在法庭上皆川夫妻比鄰而坐,口中呢喃誦念著佛經的妻子朋美眼神渙散,和從表情絲毫感受不到有任何悔意的丈夫忍,兩人應訊時的態度,加上答辯時使用的詞彙和肢體反應,倒是讓辯護律師得以用「兇嫌那是在深刻地反省自我」的理由來辯解。然而,每個下一次的偵訊和出庭,就像是又多撕開了一層隱形的包裝外衣,越是往裡頭探見,越讓人注意到當中的殘虐與悲哀。即使最終皆川夫妻都被判了刑,兩人的表情和反應依然沒有改變。
六名孩童加上夫妻,這一家八口最初是住在埼玉縣的草加市,後來搬遷至東京市的足立區。2014 年 5 月 14 日,日本兒童福利諮商機構(兒童相談所)接獲通報,懷疑皆川家的小孩下落不明;兩天後,兒福機構指派數名職員訪視皆川家。就在進屋前,丈夫皆川忍先是向對方表明,自己的妻子朋美因有孕在身,正躺臥著在休息,故不便起身相迎。 訪視專員沒多想便跟著進到屋內,而打開門後,先是一陣異臭直衝上鼻,讓人不敢相信這是他們稱之為「家」的住所。
昏暗的燈光下,依舊能看見屋內到處是髒亂不堪的景象,用來關寵物的籠子、散落一地有髒汙的衣服和毛巾,和那陣許久不散的味道,很明顯的是養過十多隻狗的動物臭味;寢室門一打開,橫躺在前的是正懷著第七胎的朋美以及其他幾個孩子。被單上都是斑點汙漬,但這裡卻是這一家人睡覺休憩的地方。接著,訪視人員大概清點了一下屋內的人數,確認無誤後,沒多做停留便離開──直到返回兒福機構後,開始愈想愈不對勁,再透過其他途徑去確認,才驚覺當時看見的可能是——偽裝的人台。
擔心事跡敗露連夜潛逃,途中不忘虐待次女
5 月 30 日,由於訪視必須先事前通知,兒福機構擔心會被以同樣的理由──朋美有孕在身,不便見外人──給拒絕,甚至還會給他們有充裕的時間預作準備,因此決定依照規定,對皆川家提出「全家人必須到場諮商」的要求;若他們拒絕,兒福機構是能直接進到屋內檢視的。接到通知後的皆川夫妻,隔日先是將家當行李運出,然後在次日凌晨,開著車全家人連夜從東京市區潛逃到千葉縣木更津市的小旅館,餓了就到附近的超商或超市隨便買點東西吃。倉皇逃跑又缺乏計畫性,皆川夫妻將心中的鬱悶全發洩在次女身上。
皆川一家人躲藏在飯店期間,母親朋美因為懷孕而沒什麼食慾,就把沒吃完的炸豬排丼飯擱在電視機上。四歲大的次女玲花因耐不住飢餓,顧不得那些被告誡的「規矩」,直接把那便當拿來吃。皆川忍發現後,立刻一手把她抓起來、另一隻手直接往她幼小的臉蛋揍了不下數拳;玲花哭求父親原諒,卻還是被父親用狗項圈鏈住她的脖子。幾天後,全家人開車移動到東京灣,皆川夫妻倆帶著孩子們到高速公路休息站旁的拉麵店吃飯,唯獨留下玲花一個人,把她關在車內。
餓肚子的玲花,又趁著家人不在,偷偷把車上其他小孩的果汁拿來喝掉;沒想到遇到吃飽回來的家人,皆川忍為此再次暴怒,直接從車外一腳從玲花的臉踹下去。小小的身軀禁不起大人的腳力,她的脖子上還繫著項圈,避無可避,直接整個人摔進車內。她的嘴角邊一條條鮮紅的血就這麼流了下來。當天夜裡,皆川一家人在開車途中,被東京都荒川區的巡邏警察給攔了下來,並在盤查後立刻加以逮補。然而他們被逮補的理由竟是朋美當時無照駕駛;此外,他們先前從足立區潛逃時,把承租公寓裡的冷氣順手給搬走,因此身上還背著竊盜嫌疑的罪名。
因無照駕駛落網,車內唯獨不見次子
夫妻二人遭警方臨檢後逮捕,車上的其他孩童經過醫療人員的詳細檢查後,就被送到兒童福利諮商機構安置,而根據醫院公布的檢查結果,玲花因為長期沒有攝取足夠的食物及營養,不僅體重比一般同齡的女孩要輕,甚至幾乎無法靠自己的力量站立;眼睛浮腫、鼻子出血,身上還有多處的瘀血、傷疤,更別提當玲花從車上被接送到醫院前,那條仍繫在她脖子上限制行動的狗項圈。
在竹之塚警察署負責偵訊的是警察廳搜查一課,針對兒子玲空斗的下落做進一步的詢問,而皆川夫妻兩人口徑一致地說:「小孩是自然死亡,所以決定把他的遺體運到河口湖附近埋了。」但可想而知,無論是警察或是兒福機構都認為他的死因並不單純,於是希望能從他們夫妻口中套出確切的棄屍地點,若是在遺體身上找到有凌虐的痕跡,就可以當作證據,依傷害致死的罪名將兩人起訴。
「屍體」成為這起事件中最關鍵,也是重要的一項物證。但無論警方派出再多的警力,前往他們所供稱的棄屍地點搜索,卻仍找不到玲空斗小弟弟的屍骨。
面對檢調的詢問,夫妻僅承認對次女玲花曾經管教過當,兩人的供詞之間甚至也有些微的差異。妻子朋美說,她雖然看見先生對孩子們施虐,但因為太害怕而不敢替孩子們解圍,這些全都是先生忍自己一個人做的,自己更是因為有孕在身,導致身心都極度不穩定,根本無法下手做出這些慘忍的事情;皆川忍則供稱小孩是自然死亡,當下沒有立刻通報的原因,則跟他自己過去在社福機構不愉快的童年經驗有關,認為倘若這件事被兒福機構知道,一家人可能會面臨被拆散、四分五裂的命運。
口拙人緣不佳的牛郎,與毫無酒店味的女公關
長相普通,說話談吐一點也不像牛郎的皆川忍,和身上不帶有一絲風塵味,體態容貌可說皆低於酒店公關水準的妻子皆川朋美,是因著什麼樣的原因或理由,才深深地受對方給吸引呢?法庭上面對檢調雙方的詢問,時而沉默不語、時而又只是隨便應和,因此警方一直無法掌握到事件的所有真相。同時,拘役期間的朋美多次癲顯發作,加上疑似精神分裂的情況,為治療而必須服用大量藥物的她,在法庭應訊時多半無法正常地立即做出反應。
關於皆川夫妻兩人最初的相遇,是在 2007 年的 5 月某日。被自己的母親帶去牛郎店消費的朋美,與當時還是牛郎的皆川忍,相識後一拍即合,儘管朋美自己也在從事陪酒的行業,且不久之前才剛產下一名女嬰,其生父還是朋美的某位客人。也因為長女沒有入到對方的戶籍,朋美得以換來一筆 250 萬日幣的贍養費。自從第一次在牛郎店認識之後,皆川忍與朋美兩人很快地便決定要同居,忍先是辭掉牛郎店的工作,然後透過派遣公司的安排,進到貨物配送的服務業。
另一方面,朋美則是專心當起家庭主婦,一邊照顧著小孩。直到被警方逮捕以前,這對夫妻以每年一個孩子的頻率,陸續生下了六名子女。不過光靠皆川忍的派遣工作,實在無力負擔一家八口的生活,不久他就辭去正規的工作,開始誤入歧途,透過其他不正當的方法獲取金錢。2011 年,老二玲空斗曾發生過交通事故,當時雖沒有直接被車子碰撞到,但夫妻捏造事實,說次子玲空斗因被撞傷而必須要到醫院作治療和檢查。皆川忍對保險公司隱瞞自己已離職一事,拿著過去派遣公司的請款單據,向保險公司前後共詐領七次、獲得約 16 萬日幣的保險金,並且還偷奶粉去變賣換現金。
最後,因為上述這些詐騙與竊盜的行為,皆川忍被警方逮捕並判刑,此時,一家人唯一的經濟來源受到影響,老二玲空斗暫時被送到埼玉縣的兒童福利諮商機構安置,而他們一家的困境正好符合政府育兒津貼的補助條件,於是該機構的職員便建議皆川夫妻提出申請──光是這樣,他們一個月就能有 30 萬日幣的補助收入,比起派遣的工作薪資整整多了一倍。之後他們就以相同的手法,依照小孩的人頭數繼續向政府申請補助,每個月至少有 40 萬以上的收入。
在毫無金錢觀念的隨意揮霍之下,夫妻兩人每月只顧吃喝玩樂,絲毫沒有將補助津貼妥善用在照顧小孩身上,甚至還跑去借錢,最終導致破產。此外,埼玉縣的越谷兒童機構曾接到朋美母親的聯絡,說是自己的孫子疑似受到虐待,要他們到皆川家訪視;最後兩夫妻決定帶著全家人連夜搬家,逃到距離僅只十分鐘車程外、地點劃分在東京的新公寓,也就是這起事件發生的地點。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