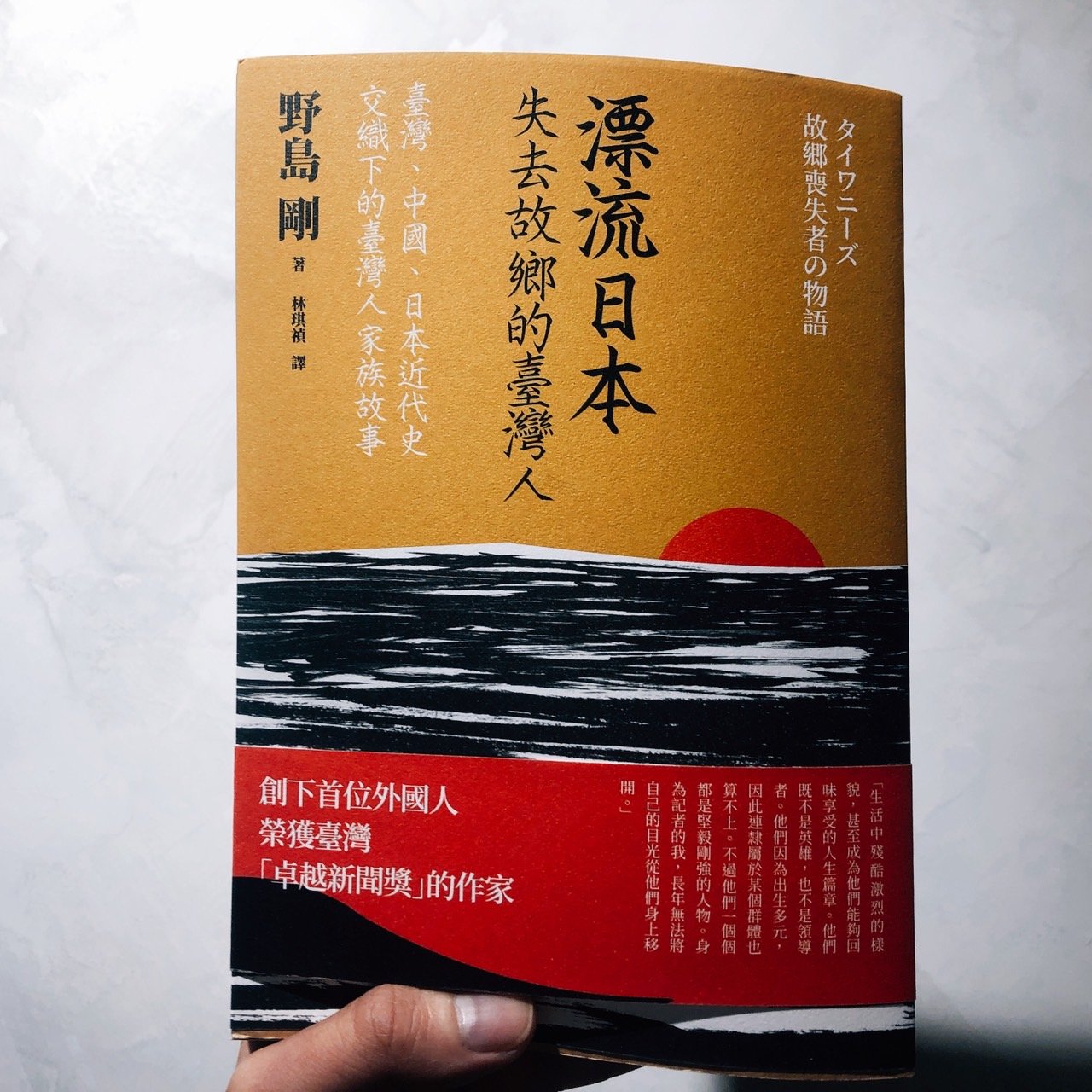乍看這個案子並不特別,就只是近年來常聽到的那種故事:因為DNA檢驗技術突飛猛進,警方從陳年證物上找到蛛絲馬跡,終於比對出某件冷案的兇手。而且此案兇手似乎並不像「金州殺手」那樣作案無數,所以身分被揭發也激不起太大的水花,超過40年的追兇歷程,如果「講重點」,可以用五百字就說完,而其中可能有三百字是在渲染屍體被發現的狀態多麼古怪。
但一個人的死,從來就不真的只是「一個人的死」。阿莉絲・培理的死亡,牽動了無數人往後的生命軌跡。真正的故事在那裡。
-1024x544.jpg)
她只是去教堂祈禱
1974年10月12日,一個星期六的晚上,阿莉絲・戴基瑪・培理(Arlis Dykema Perry)跟她的大學生丈夫布魯斯・培理(Bruce D. Perry)在史丹佛大學校園裡散步,途中為了要不要檢查汽車的胎壓,他們起了點小爭執。布魯斯決定回家,信仰虔誠的阿莉絲卻說她想去史丹佛紀念教堂祈禱,於是夫婦兩人在晚上11點左右分開。然而過了午夜以後,阿莉絲還沒回來,布魯斯開始擔心了,開車繞校園找人也沒找到,只好在凌晨三點半打電話給警方,請他們幫忙找尋失蹤的阿莉絲。
布魯斯與阿莉絲都是1955年出生的北達科塔州人,今年還不到二十歲,他們高中時就是那種經典款情侶檔:男生是運動健將,女生是啦啦隊員。阿莉絲的父母原本不太贊成小女兒這麼早婚,最後還是拗不過他們。這對夫婦結婚至今還不過三、四個月,一切都還是新的,連吵架都很新鮮。她只是去教堂祈禱啊,教堂12點就鎖門了,為什麼會一整晚不見人影?布魯斯在家焦慮不已,只希望這一切有合理的解釋,只要找到她就會知道了。
即將破曉的時候,警察來敲門。他們要布魯斯到警局填正式的失蹤報案表格,然而行動卻急迫到不讓他去換衣服,他只好在寒冷的清晨穿著短褲跟T恤去警局。進了警局以後,警察一開口就嚇壞了他:「我們知道你太太有外遇,而且你發現了對吧。」「她跟你說她懷孕了,然後你就控制不住憤怒,是這樣吧。」在兩小時的誘導與盤問之中,驚恐的布魯斯問了好幾次:「我太太在哪裡?」沒有人回答他。
到最後,是負責替布魯斯採指紋的警方技師,告訴他阿莉絲出了什麼事。
嫉妒的丈夫,還是可疑的夜班警衛?
阿莉絲死了。她陳屍在教堂內靠近聖壇的長椅下,顯然承受過性侵與高強度的暴力對待,事後兇手還特別擺弄過屍體。她的眼鏡不翼而飛,有可能是被兇手帶走。〔為求記錄完整,以下將說明屍體損傷細節,但跳過也不影響下文閱讀,請讀者自行斟酌,欲閱讀者請選取反白:有一根手柄不見了的冰錐敲進了阿莉絲的後腦勺,這是致命傷,但她脖子上還有勒痕;她的身體上有被毆打性侵留下的痕跡,下半身赤裸,下體被插入一根白色蠟燭,還有另一根白蠟燭放在她的胸部之間,這些蠟燭是從聖壇上取下的。由於阿莉絲的遇害地點與屍體狀態,有些陰謀論者真心相信此案是神祕的撒旦信徒幹的好事,這當然是無稽之談。說真的,多的是人類不需要任何邪惡信仰誤導,光靠自己的純粹惡意,就做出性虐活人或褻瀆屍體的行為。〕
發現她的人是史丹佛夜班警衛史蒂芬・克勞佛(Stephen Crawford)。根據克勞佛的說法,他在23:45關閉了當時空無一人的教堂,把每一扇門都鎖上了。凌晨兩點巡邏時經過,門也都還是上鎖狀態。然而在13日早上5:45左右,他去替教堂開門的時候,發現西側門從裡面被人硬是撬開了,進去以後就發現屍體。
-300x200.jpg)
聖塔克拉拉郡(Santa Clara County)警方做了謹慎的蒐證與過濾。對他們來說,最可疑的人還是死者的丈夫布魯斯,還有遺體的第一發現者克勞佛。稍微看過一些刑偵推理故事的人,大概都可以理解這種推論背後的邏輯:如果是情殺或仇殺,配偶總是最可疑的,尤其阿莉絲這樣一個單純的鄉下女孩,來到史丹佛才一個多月,認識的人屈指可數;如果是陌生人見色起意,滿有可能就是第一發現者在故弄玄虛,而且克勞佛本來就是掌握教堂鑰匙的人。
意志堅定的布魯斯與空軍退伍軍人史蒂芬
這兩位命案重要關係人,是怎麼樣的人呢?
布魯斯是個意志異常堅定的年輕人:他小時候有氣喘病,卻努力靠著想像練習(專注於呼吸、想像肺部充滿空氣、克制恐慌)減少發作,成為傑出的高中田徑選手,因此拿到史丹佛大學的體育獎學金。當初純樸的布魯斯只知道史丹佛有奧運名教練,壓根不知這裡是學術頂尖名校,不過就在大一這年,他上了知名神經內分泌學家西摩・列文(Seymour Levine)的課,因此確定了他的學術興趣:他想更深入研究壓力造成的生理影響。
在度過辛苦充實的一學年以後,布魯斯在暑假回鄉跟阿莉絲完婚,然後在9月帶著新娘一起搬進史丹佛的已婚學生公寓。他繼續讀大學,阿莉絲則開始在一家法律事務所當櫃檯接待員,事發時她不過上班兩星期。
那年夏天他們才承諾要相伴一輩子,怎麼也沒想到還不及半年,死亡已經把他們隔開。
另一個命案關係人,夜班警衛史蒂芬・克勞佛,當年是個28歲的青年。他是空軍退伍軍人,1971年加入史丹佛大學公共安全部門(Stanford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擔任佩槍警官。所謂的「公共安全部門」,指的是一種統包性的州政府或地方政府單位,警務、消防、急難救助等等廣義的公共安全事務,都由這個單位管轄。
史丹佛公共安全部門的管轄範圍就是校園內,執法權力是來自史丹佛大學與聖塔克拉拉郡警之間簽署的法律備忘錄,必須遵守州法律與郡地方條例,可以進行逮捕。到了1972年,新上任的主管決定重新檢討員警的佩槍資格,結果有四分之三的人被刷掉,克勞佛也是其中之一。這些人可以選擇轉任不佩槍的校園警衛,克勞佛雖然滿腹牢騷,還是接受了這種「降級」,繼續在熟悉的校園內工作。
警方從陳屍處的白蠟燭燭身上採集到一個掌紋,還從屍體下面的祈禱用跪墊上發現精液痕跡(當時沒有DNA檢驗技術,只能藉此找出血型),然而經過比對以後,跟布魯斯還有克勞佛都不符。明顯肝腸寸斷的鰥夫布魯斯通過了測謊,正式被排除嫌疑。克勞佛也通過測謊,警方找不到任何證據能積極證明他的說詞不實,只能把他放到一邊去,繼續清查其他可能性。警方甚至設法把可能犯案時間內出入過教堂的每個人都找出來了,卻毫無所獲。
有一位FBI側寫師推測,兇手年齡在17到22歲之間,習慣獨來獨往,會寫詳盡的日記,還喜歡從命案現場拿走「戰利品」,但警方並未找到符合描述的人。連續殺人魔泰德・邦迪(Ted Bundy)落網後,警方一度懷疑他也殺了阿莉絲,然而加油站收據證明案發時他不在場;惡名昭彰的「山姆之子」大衛・伯科維茲(David Berkowitz),入獄後自稱在邪教聚會裡見過殺死阿莉絲的兇手,然而警方查核以後,發現伯科維茲又是在瞎扯求關注。
案情就此陷入膠著,彷彿跟著阿莉絲一起陷入死亡的長眠。只有還活著的人,繼續被無情的時間往前推。
25年能夠如何改變一個人
在如此殘酷的狀況下失去妻子,親友們同情布魯斯,也希望他能夠早點振作。他們建議他盡快恢復生活常軌,繼續讀書,盡可能別去想阿莉絲的死。布魯斯卻沒這麼做,他暫時從史丹佛休學,到處漫遊了幾個月;他口袋裡沒多少錢,通常借宿在親友家,偶爾甚至要露宿街頭。他花了很多時間去想已經發生的事。他在1992年的一則訪問裡提起當年:
「有時候我覺得我好像置身於一部電影裡——偶爾我會這麼想:『老天爺啊,我真不敢相信這種事現在還在繼續。』我長時間感受到痛楚哀傷,還會想著這一切實在太不公平。我試著去想像到底是什麼讓人幹出這種事。起初我滿腔怒火——但我不知道要往哪發洩,因為我根本不知道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某種程度上,我還得要捏造一個發怒的對象。後來我就乾脆放棄這麼做了,這樣是在妨礙我繼續過日子。當我接受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以後,殺死她的人長相如何、為人如何,就不再那麼重要了。」
布魯斯後來並沒有發展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就他自己的分析,應該是因為他當時選擇直接面對創傷。有研究顯示,如果說服戰場上的士兵在戰鬥過後立刻反思並討論他們的感受,就比較不會發生PTSD。撐過最痛苦的階段以後,布魯斯發現自己的性格有了改變,變得更有自信——因為他想像不到,他還能碰到什麼事情比他已經經歷過的還糟?而且事實是,他熬過了喪妻之痛,甚至還能再度感到快樂。他覺得自己更成熟也更自由,更不在乎一般的社會價值觀。
他重回史丹佛讀書,但周遭知情者的同情目光讓他很不自在,於是決定轉學到麻州安赫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他在那裡盡情上他想上的課,沒有理會畢業所需的學分要求,然而在沒拿到大學文憑的狀況下,他還是於1977年成功申請上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醫學院,一路讀到取得博士學位;後來他同時兼顧臨床與研究,成為專門研究兒童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兒童精神科醫師。
在1992年接受訪問的時候,37歲的布魯斯・培理已經建立了新的家庭,過著忙碌充實的生活。他承認這段經歷讓他對病患更有同理心,但堅持早在阿莉絲過世之前,他就已經對PTSD這個領域產生興趣,如果阿莉絲沒有死,他可能還是會走這條路。在他現在的生活裡,許多人都不知道他年輕時的慘痛經歷。

同樣在1992年,另一個命案重要關係人史蒂芬・克勞佛,卻是落入被警方逮捕的窘境——雖然他在1976年就離開史丹佛了,但直到此時才被人發現,他在職期間從史丹佛的人類學系及圖書館裡偷走了一些美國原住民工藝品跟雕像,還有近兩百本珍稀書籍。
他被捕後供稱他對校方及警方把他當成阿莉絲謀殺案的嫌犯感到憤怒,所以偷這些東西算是報復,結果被判緩刑6個月。
在這件尷尬事發生的第二年,他搬進了聖荷西的一棟公寓,成為一位「看起來人很好,但不太跟其他人打交道」的房客。
25年後,他就是在這個地方死去。
DNA技術與從未放棄的警探,令冷案重啟
雖然沒有新發展,還是有許多人惦記著這個殘酷的案子。2014年,聖塔克拉拉郡警在《史丹佛日報》(The Stanford Daily)對此案的四十年回顧報導裡,表示他們一直都還在積極偵辦中,而且現在有新的科技可以處理舊證物,或許能找到新線索。這可不是空口說白話;數十年來警方一直跟所有關係人保持聯絡,戴基瑪家與克勞佛都不時會接到警方的詢問。
2016年,聖塔克拉拉警方又開始積極約談克勞佛。他們從阿莉絲當晚穿著的牛仔褲上殘留的精液裡,驗出了DNA。這時候的克勞佛,已經是個身體狀況不佳的獨居七旬老人,這一波約談的壓力,讓他寫下一張潦草的自殺遺書——但此刻其實還不是終點。他還有兩年。
2018年,聖塔克拉拉警方終於準備好充分的證據,可以逮捕克勞佛。於是在6月28日早上,警方出動去克勞佛的公寓逮人。克勞佛聲稱他需要幾分鐘時間換衣服。
換什麼衣服?44年前那個寒冷的10月清晨,謹慎的警探們就怕可能有殺人嫌疑的鰥夫趁隙逃跑,甚至不讓布魯斯・培理有機會搭件外套。如今來逮克勞佛的警探們也怕節外生枝,沒有等他自己出來,他們就用房東提供的鑰匙開了門——然而一進屋,他們就看到克勞佛坐在床上,手裡拿著一把槍!
克勞佛的住處空間狹小,警探們緊急撤退,然而他們退出門外不久,就聽到屋內傳來一聲槍響。44年來從沒坐過一天牢,卻也從未真正自由過的克勞佛,一槍打穿了自己的腦袋。
有些疑問,終究無法解開
儘管兇手什麼也沒說就死了,有了DNA證據,聖塔克拉拉郡警長蘿瑞・史密斯(Laurie Smith)還是宣布此案已偵破,同時表示此案發生前一年她才剛到警局服務,阿莉絲只小她幾歲,她一直對此案有很切身的感受。最後了結此案的警官李察・阿蘭尼斯(Richard Alanis),則始終把阿莉絲的照片放在自己的皮夾裡,提醒自己,她的生命跟這個多年冷案是有價值的。
破案消息傳出後,已經有了新家庭的布魯斯・培理對媒體保持沉默,或許不想再挖舊傷疤;而阿莉絲已經88歲的母親珍(Jean Dykema)雖然感激警方終於破案,卻很遺憾兇手沒有再早一點抓到,因為阿莉絲的父親馬文(Marvin Dykema)已經在三個月前亡故。他在世的最後幾年,或許是自知來日無多,急切地想知道到底是誰殺死了他的么女。苦求真相而不可得,他是帶著遺憾死去的。
克勞佛的死,讓許多問題再也沒有答案(好比說他的作案動機、是否還有其他受害者——就目前的發展來看,似乎沒有)。但至少,對於現在還活著的、被這個死亡牽動的所有生者來說,阿莉絲的故事總算有了確定的結局。真正的平靜長眠,現在終於開始。
後記:
布魯斯・培理醫師的其中一本著作是有中譯本的,舊版叫做《在狗籠裡長大的小孩》,絕版已久,我非常喜歡那本書,因此去查了一下維基百科,想知道他還有什麼別的作品,卻意外發現他早年的創傷歷史,震驚不已。去年另一家出版社柿子文化出了此書的新增訂版中譯本,改名叫《遍體鱗傷長大的孩子,會自己恢復正常嗎?》,我入手之後,惦記起這樁冷案,就再去查詢了一番,然後又嚇了一跳:這案子竟然被偵破了!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案子雖然有著遙遠的時空阻隔,對我來說也有某種個人意義。
資料來源
“Murder at Memorial Church remains unsolved 40 years later”
“Suspect in 1974 Stanford church slaying kills self with detectives closing in”
“Sheriff: Grisly 1974 Stanford murder solved”
“Sheriff: Suicide note, serial killer book jacket at murder suspect’s home”
“Past detectives on Stanford chapel slaying reflect on case’s ending”
“Authorities solve 1974 campus murder”
“After 44 Years, DNA Solved the Satanic Murder of Arlis Perry. Was She the Only Victim?”